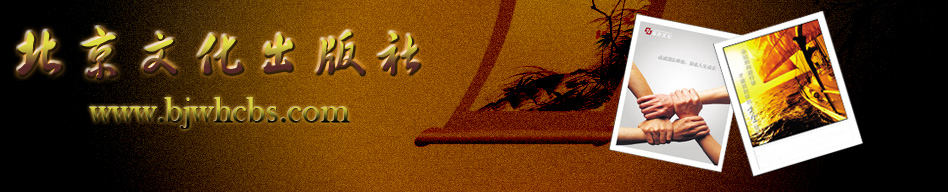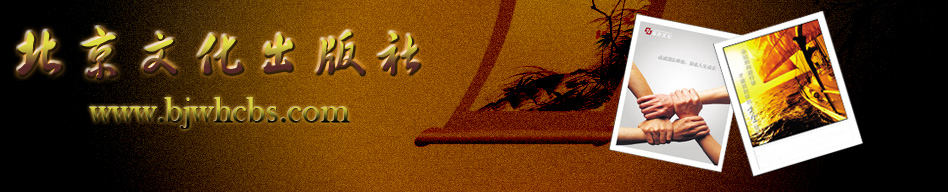童年的磂沙河
文/宋添贵
时光总是在人的不经意间流走,一晃,几十个年轮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
随着日月的斗转星移,宋向阳孩儿时的记忆不时地在他的脑海中涌现了出来。为什么会这样,这也许就是岁月无情顾及你,凡人无故自多情吧。
多年以后,他带着一股乡愁,一种思念,一腔的疑问,一脑的诚惶回到了四十六年来欲长居但未常住的乡下家里——棉洋镇磂沙河畔的高寨哩。
高寨,顾名思义,即是在高高的山顶上建房聚合而居的村寨。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生产队的建制,现在是村委会下的一个自然村。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旧社会,粤东山区是世人称之为“南蛮”之南的地方,穷山恶水,山高路陡,树林茂密,人丁稀少,把房子建造在山顶上,既有预防野兽来犯之功又有抵御外族人入侵之效。结寨居住,易守难攻,是封建社会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常识。
未常住,也就是父辈有祖屋,因长期在外工作,只是偶尔回来住上几晚。对宋向阳来说,高中毕业以后就入伍从军直至退休,长则几年,短则几天,都以探亲、或以陪伴父母为由暂居几日。退休后又向往儿子工作的大城市,以带孙辈为由,像其他同事一样出去“屙山屎”,并且老了才“出家”,学着别人在纸上写写,在笔下划划,圆所谓的“作家梦”,恍恍四年多就过去了。今天,国庆节刚过,因为老家杂七杂八的事情需要处理,所以就趁着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免费回来,省了两百多元过路费,正式以“村民”的身份住下。没有想到一住就两月有余。
家乡的梦,梦里的家乡,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山清水秀”这句成语似是专门为磂沙河畔的山村所造。
梦中的高寨哩下面有条磂沙河,一河两岸,麻竹、斑竹、绿竹、青皮竹成堆,灌木花丛种类繁多,绿意盎然。春天来临,竹笋破土,它任凭风来雨去,无拘无束,不久就钻入了蔚蓝的天空中;相映衬的布惊树,像排着队似的一丛连着一丛,伴着哗哗流过的河水悄悄地发出了嫩芽,此时偶尔有村民来采摘做布惊茶,平时有人跌倒碰伤,皮下有淤血就摘来几片布惊树的嫩叶双手揉搓一下后在患处擦,可以当跌打用药;还有带刺的金樱子更像是刚从梦境中惊醒似的,一夜之间就快速伸展拳脚,把绿枝蔓延到河床上面。待到四至六月,青竹随风摇摆,杨柳丝丝舞动,数不清的灌木花朵,红的,白的,黄的,紫的竞争开放,那景象就是“百花映陌上,千绿醉岸边”,满眼处处都是春意,绿色绿到了极至。
磂沙河东岸的山脚处,农家瓦屋座座相连,早晚炊烟袅袅,百鸟和鸣。岸上的238省道逶迤,沙粒公路汽车过后冒出了一股股的“白烟”,有如烟雾飘荡在山谷里的曼妙之景;西岸堤内的百亩稻田,禾苗生长期墨绿遮眼,一望无际,收割期稻浪滚滚,金黄一片。
宋向阳童年时的高寨哩,全寨人都已搬离,把房子建到了寨顶四周及磂沙河两岸山岭的坡脚处,由此山寨变成了村落。在模糊的记忆中寨顶上只剩两间破烂不堪的泥墙屋,记得有一个叫湖叔公的还住在那露着日光的瓦房里。
据说,往前就难以考究,近代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后,高寨哩的人都是非常贫穷。穷到什么程度,有一个现象可以佐证,那就是解放后在划分出身成分时,全寨的几十户人家都是贫农以下,还有几户是雇农,一户中农都没有,就别说地主富农了。“文革”时期有人贴过一副对联,上联是:家家一贫如洗,下联为:户户四壁萧条。以示穷了还光荣。
不过,往日高寨哩的兄弟祖叔,生活虽然贫穷潦倒,但人情味却是很浓,性格也很开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没有那么多的转弯抹角。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座上五下五两杠横的大瓦屋,住着七八户人家,几十人聚居在一起,白天生产队劳动,早晚各自围园种菜,锄地种木薯种番薯,了理家务,都是互帮互谅,气氛融洽。家什物品虽是各有其主,但也是互通有无,有了问题都是协商解决,矛盾较少,互相吵骂的现象很少发生。寨哩十几座屋的村民你来我往,孩童过家玩耍,打扑克,“磊榄弗(核)哩”,“打石哩”,大人坐嬲喝茶,谈天说地是常态。共屋的裕先伯父有一间闲嬲房,经常半夜三更灯火通明,宋湘、李文古等人的故事被寨哩有点墨水的人描述得诙谐风趣,生动幽默,特别是大湖洞哩的安仁叔公过寨来“夜吹”之时,裕先伯父拿出正春茶招待,他便是妙语连珠,把《三国演义》《水浒传》里故事说得奇趣横生。那时,笑看世事,淡泊人生是当时村民们自我修持的境界。
当年,宋向阳父亲与裕先伯父共建的“文仁楼”瓦屋高于238省道约五六十米的半坡上,大门朝西,门坪下的公路边就是磂沙河,北边一公里外的山腰上有一座座北向南、远眺莲花山支脉松岗嶂山峰,近视磂沙河哩大尖石的完小学校。那是宋向阳人生求知的第一座母校,名叫化育小学。
学校的正前方,磂沙河拐入高寨哩转弯处的右侧,有一个大大的尖石巍然屹立在那里。这块大尖石,远看像是一颗大大的四方印章,人站在下面显得非常的缈小。尖石旁有户人家,主人叫阿凤伯,他家附近有一祖坟,阿凤伯有一个儿子在县委任秘书职务,掌管着当时的县委大印。某日邻村的一位风水先生路过该地坟,他在地坟中央遥望四周层峦叠嶂的山情和“来龙去水”后侃侃而谈,把主人的儿子在县委掌管大印与磂沙河里的那块大尖石联系了起来,他说:尖石自然生成在其祖坟的右下方,就如右手握着大印,尖石在河里,河里有水即如“印油”啊,盖起章来方便得很,然后又把化育小学的校门直视松岗嶂山峰和那块尖石是如何如何的好,将来一定会出人才等等说道了一番。吹得神乎其神,像真的一样。
大尖石,天然自成,巧夺天工,一听就知道其特征是“尖尖”的。它是一个锥形体,但不是圆锥形,底部是不规则的四边形棱锥座,往上伸展的棱角直线到了顶端自然交汇,底座面积近百平方,高约有十多米。
童年的磂沙河,河面宽阔,两岸的河滩常年绿草如茵,那是宋向阳的放牛之地。河水缓流,平时水位没过膝部,水道勿左勿右,洪水时往往早上还在东流,傍晚就流到西边去了。趟过河道时能看到许多小鱼逆水争游,大部分是两指大小,有时也能看到像巴掌那么大的鲤鱼等。
记得长到八九岁,宋向阳就跟着比他大的伙伴去拦河捕鱼,再长大一点就开始自己单干,这样收获多少都是归自己所有。拦截河径捕鱼也需讲究方法,要先细心观察。选择有许多小鱼在闲游的支流为目标,然后走到上游河水的分岔处快速用河沙截住流水,并马上跑到下游用“河哩”(竹篾编成圆筒,鱼只能进不能出)拦住鱼群,再从上往下慢慢追赶鱼群往“河哩”钻,最后从“河哩”取出捕获的鱼,用双手拿捏干净鱼肠等,洗净回家,满心的欢喜。
他偶尔也学着大人想从流动的河水中抓到鱼来,但他的技巧不行,从来空手没有套住过“白狼”。反而用双脚在水流中用力翻滚沙粒,会翻出许多“沙钻”(一种钻在沙粒浅层的鱼)来,这种鱼一旦从沙粒下出来就会伏身在沙粒表面,很容易捕获。
孩童时光,过隙白驹,到十三四岁宋向阳就用“鱼藤水”到河堤下面去毒鱼了。“鱼藤水”毒鱼要先在家里把一种有毒性的“鱼藤”敲打榨出汁来,加适量的水,选择估计藏有鱼的水潭,然后将“鱼藤水”倒进去,接着使劲搅动静态的潭水,让“鱼藤水”的毒性充分渗透到深处,一会被毒昏了的鱼就会“扁白”(翻身)跃出水面。此时,就必须快速用竹篓子把鱼篓起,不然几分钟过后“鱼藤水”的毒性失效,鱼很快就会回游到深潭中去,转眼让你前功尽弃,变成竹篮打水。此种方法,如遇洪水刚过不久,碰到了藏有多鱼的水潭,那一定是个丰收的场面。他的记忆中有过几次是鱼满水桶,收获颇丰,每次都让全家人美味了一顿。
大尖石上游右岸的山坡山窝山岗处,那里是寨里村民的菜园和畲地。居住在东岸的村民,夏天趟着过膝的河水去锄畲种豆,种瓜种菜等等的劳作,河里没有桥梁。但到了冬天的寒露节气前后就会有好心的村民砍来松树或者麻竹,架起便桥供村民通行。架桥人的这种善举从来都是自愿效力,不计报酬。事后宋向阳发现他们的行为深受村民的赞赏,故而也就影响了他美好人生观和道德观的形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磂沙河流域森林植被很好,满山遍岭都是松树和杉木,雨水充沛,河水的径流量很大,每年的端午节过后就开始不断地发洪水,等到六七月份大洪水必然不期而至。洪水有时淹过河床两旁的淤滩地,有时冲上堤坝,甚至涨到了238的省道公路上。
每次洪水退去之后的尖石下游,因迅猛的怒水冲撞大尖石的物理作用,旋涡后形成了深不见底、湛蓝湛蓝的水潭。大洪水大水潭,小洪水小水潭。小潭面积二三百平方,水深七八米,大潭面积七八百平方,水深十几二十米。每当有水潭出现之时,宋向阳就会想到最后搬离寨顶那位湖叔公警告孩子们说的话,他说:“你们不要靠近水潭,不然人一站到水潭边上就会一桨(移动)到洲(远)啊。”意思是大洪水旋转上来的那些沙粒是松散不实的,人若靠近就会连人带沙陷进到深潭里,危险得很。
湖叔公虽然那样说,但对于像宋向阳这些生长在一河两岸,掌握了一定游泳技巧的孩子们来说,水潭就是再好不过的天然游泳场,他们喜欢渴望的就是这深深的潭水。这些十四五岁的年青人,只要等到洪水退去,就会急不可耐地凑到一起,三三两两前去一展游泳的技能和快乐。当然,他们会选择靠岸坚实的堤边下水。因为他们从八九岁开始就学游泳,到了此时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什么蛙泳,自由泳,仰泳,蝶泳,样样的姿势和技巧都是了如指掌。
他们到了水潭里,一般先各自变换着姿势自由游一会,然后就分组轮流比赛。什么顺水游,逆水游,横游,圆圈游,水中站立和潜水耐力比赛,项目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个叫阿政叔的后生哥,他的游泳技术好,游姿自然,既游得远速度又快,水上的站立功夫又强,还能下潜到水潭的底部,每次的单项冠军和全能冠军基本上都是他获得。当然,伙伴们的“冠军”称号只是口头奖励,他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过后还必须从家里偷来花生、爆米花之类的食品馈送给大家,不然大伙就会说“这次没有吃的,下次不跟你玩了。”
说到这位阿政叔,记得有一次发洪水前村民们到西岸边远的山嶂里去耕作,傍晚回来时遇到磂沙河流域暴发大洪水,整条河流波涛汹涌,洪水淹过了堤围,两岸一片汪洋,东岸的村民无法回到家中。见此情景,东岸的叔叔伯伯,大娘小婶,兄弟姐妹们只得投靠在西岸的亲房祖叔家里过夜,唯有那个叫阿政叔敢冒着满河大水横渡过去,有惊无险地回到了东岸自己的家里。后来,那个阿政叔因为既爱读书又懂事,所以常受到寨哩大哥老伯的称赞,自然就成了宋向阳的崇拜偶像。阿政叔初中毕业后去化育小学当民办老师,后来靠他的努力不断受到领导的重用和提拔,直到中学校长的位置上才退休。
日升月落,桑田沧海。这次宋向阳以“村民”身份回乡居住,两个多月来,宋向阳每天散步于磂沙河两岸,早晚流连忘返于大尖石的附近,凝视,追寻……
如今的高寨哩已经没有了“高寨哩”的含义,只剩下徒有其名。寨场与四十多年前相比,周围的山虽然还是绿色,但树木少了;村民的生活质量虽然高了,住上了楼房,但互相之间来往少了,同寨人也成了似曾相识。
当年的磂沙河水流湍急,河水清澈,小鱼成群,趟过时河水淹到大腿处;而今河床狭小,野草丛生,不见鱼虾,水浅脚踝,一跃而过。往日河里那块大尖石的四周,夏秋季节被大小深潭围绕,蓝天白云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荡漾,常有放牛的后生哥人畜同游在水潭中央;今天的尖石西边被废土围裹,泥土堆到了尖石的顶端,南边却成了村民的菜园。童年的磂沙河,脑中大尖石下面的游泳场早已一去不复返,成了他永远的梦幻记忆。
——2021.6.28于梅州坤庆楼
【作者简介】:宋添贵,男,汉族,1956年6月出生,广东省五华县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政工师,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2016年9月出版红色军旅长篇纪实小说《基建兵之歌》,2019年7月出版长篇小说《青涩的三月果》,2021年3月出版反腐长篇章回小说《曲径狐踪》。